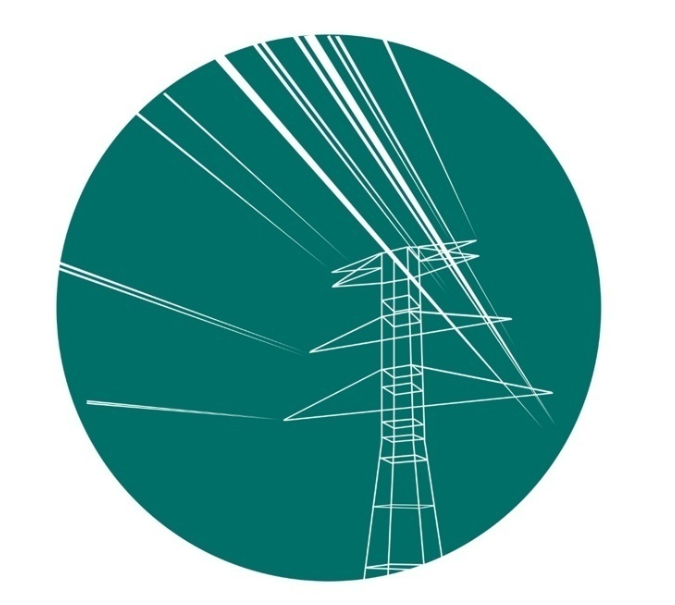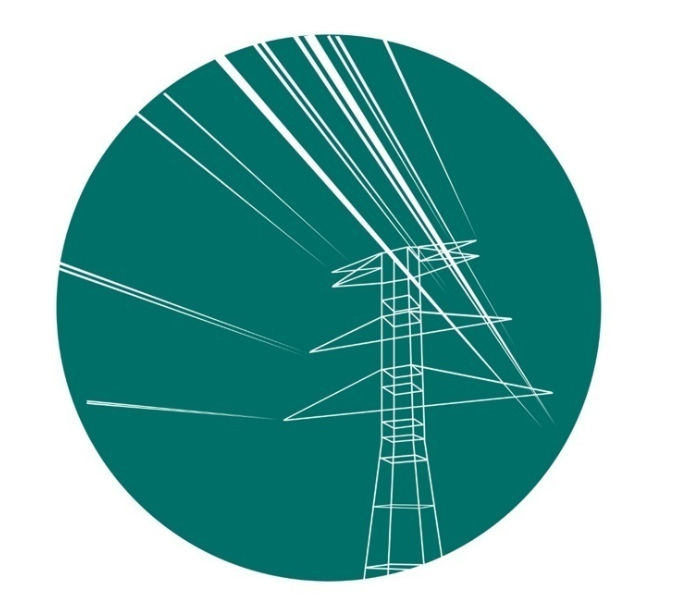与殷罡商榷|叙述巴以问题应追寻历史的全貌
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有关于近来一篇在中文互联网媒体流传广泛的文章,文章内容是我国著名中东学者殷罡教授近来有关巴以问题谈话录音的整理稿,内容经过其本人审阅。文章流传过程中所采用的标题包括《殷罡:巴以冲突的暗线与走势》、《殷罡谈巴以冲突的暗线与走势:哈马斯和伊朗不愿看到阿以和平》,以及《殷罡教授万字长文:巴以冲突的死结,是哈马斯和伊朗故意阻挠和平》等等。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15日,巴以冲突持续,加沙遭以军空袭,冒出滚滚浓烟。
上周在刚刚得知殷罡教授以万字长文分析了巴以冲突的走势时,我原本满怀期待。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期待着一些新的信息以增进自身对于问题的了解。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存在着一些信息缺失与逻辑失误。我极为认同文章结尾所言,即人们在了解与谈论巴以问题时的首要症结在于“知识、信息的缺乏”。因而我希望与读者一道重温相关事件的全貌。而在此过程中,我不得不首先指出上述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并冒昧地进行批评与补全,我想这样的过程将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巴以问题。
1.法理的另一个指向
该文结尾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应该理解一个大势:毕竟双方1993年已经签署了和解协议、“土地换和平”协议。“土地换和平”在初期进展是顺利的,如果大家都有和平愿望的话,现在和平早就该实现了。正是有人,从伊朗到哈马斯,不愿意看到奥斯陆协议的实现,不断地挑起冲突,结果就是制造了更多的仇恨。”至于我们的舆论场为什么没有看到这样的大势,该文表示:“最根本的一条,缺乏知识,没有分清情理和法理,对事态发展的过程和细节都不知道、不了解。”或者说,在殷罡教授看来,《奥斯陆协议》或“两国方案”之所以无法顺利开展,其首要原因在于“从伊朗到哈马斯”的破坏与阻挠。且因为舆论未能分清“情理和法理”,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大势。
上文所说的“情理”是一个不难理解的概念,“法理”则需要一些定义与解释。在通读文章后,我们发现,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显然是该文论述中重要的法理基础之一,例如以下一段叙述:“当年下半年,战争几个月之后,安理会通过了242号决议。其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是,‘以色列军队从最近冲突中占领的土地上撤出’……而不是要回到1948年的边界分治决议的边界。这是有法理依据的,要说清楚。”
而在回到我们关心的《奥斯陆协议》与“两国方案”问题时,依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一可以被认可的法理(即安理会2016年12月23日第7853次会议上通过的2334号决议。获14票赞成;0票反对;美国1票弃权而未行使否决权)第四条显示“完全停止以色列一切定居点活动对于挽救两国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并呼吁立即采取积极步骤扭转当地危及两国解决方案的消极趋势。”[1]也即是说,安理会认为,以色列在挽救两国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负有至关重要的责任,即完全停止定居点活动。依照我们认可的“法理标准”,该决议完全可以成为人们批评以色列破坏两国方案的法理基础,而所谓情理或许恰恰是人们在看到法理无法得到伸张后的一种表达。
展开全文
遗憾的是,长文中只有一句话提及了以色列的定居点问题,即“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定居点争议,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约旦河西岸的一部分地区还处于以色列的占领状态。”但依照我们的法理依据标准(安理会决议),西岸地区并不存在所谓“定居点争议”,而只存在“非法定居点”,且这些非法定居点正是法理中两国方案受阻之至关重要的因素。我诚然相信哈马斯是阻碍“两国方案”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他们公开的宣言。但依照统一的安理会法理标准,我们无法认定伊朗与哈马斯即是阻碍“两国方案”的主要因素、首要因素、单一因素或死结所在——因为法理明确告诉我们,阻碍“两国方案”之至关重要的因素反而是以色列的非法定居点。
2.关于1995年诸事件与拉宾之死
事实上,即便搁置以上“法理”问题,我们仍可以在该文的具体论述中发现诸多严重的信息缺失。
我想首先请大家阅读了解该文中有关《奥斯陆协议》初步付诸实践的论述:
根据协议,从1995年开始,以色列开始撤出约旦河西岸的主要城镇,先撤大城市再撤小城市,每隔一段时间就撤一个。当时以巴之间的气氛是什么呢?当时我全程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也去,一片欢欣的气氛。巴勒斯坦人说阿拉法特好样的,一领人回来,以色列就撤了。
撤离移交的过程也是很温馨的。办公室里的办公用品不许拿走,维持原样。咖啡壶里要有咖啡,个人物品可以带走。巴勒斯坦方面的人员和以色列方面的人员就是握手、拥抱、移交权力。这个移交过程中,双方老百姓一片欢欣,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除了一些非常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以外,大多数都很欢欣,甚至是喜欢阿拉法特这个人,说这老头挺可爱。
但是从以色列开始撤出之日起,每撤出一个城镇,当天或者第二天上午,哈马斯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制造一起公共汽车爆炸事件。当时还不是人体炸弹,当时没有安检,上了公共汽车以后,椅子底下扔个手提包就下车了。这爆炸现场我去过好多次,每一次爆炸现场都是激奋的、非常强硬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喊的口号就是一句话:“拉宾叛徒”。

人们在广场上悼念拉宾
当这种“土地换炸弹”重复了很多次之后,以色列的示威口号开始变了,“反对土地换炸弹”。于是在1995年11月,一个以色列的激进大学生、极端分子,叫阿米尔,在集会上把拉宾打死了。
需要肯定的是,文章为我们提供了诸如“咖啡壶里要有咖啡”一类精彩的历史细节。但这段论述依然存在着严重的信息缺失与逻辑失误。文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95年以色列开始撤出西岸,移交过程顺利而温馨,双方总体一派祥和,然而哈马斯开始恐怖袭击,导致以色列出现‘拉宾叛徒’与‘土地换炸弹’的口号,最终拉宾遇刺”。也即是说,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破坏了原本顺利的撤离工作并最终导致了拉宾遇刺的悲剧。
但这绝不是事情的全貌。让我们还原1995年巴以地区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2]:1995年1月2日,以色列政府下令停止埃夫拉特定居点(Efrat)的建设,但依然同意定居者在附近阿拉伯人种植橄榄树的山上建造500套公寓。[3]同一天里,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埃雷兹口岸射杀了3名巴勒斯坦警察。[4]1月25日,以色列内阁批准在西岸所谓“大耶路撒冷”地区建造2200套住房。针对此类冻结“政治定居点”却加速所谓“安全定居点”建设的做法,巴勒斯坦方面表示此举再次违反了奥斯陆协议,并警告称这将导致双方激进分子的暴力行为。甚至美国方面同样表示额外的定居点存在问题,可能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5]5月22日,一名以色列士兵向雅法的一座教堂发射了数百发子弹并投掷了几枚手榴弹。事件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导致教堂被毁、数人受伤并引发民众恐慌。[6]
7月24日与8月21日,哈马斯成员分别对特拉维夫与耶路撒冷的公交车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两起事件共造成十余人死亡、八十余人受伤。这是我所找到的历史记录中1995年哈马斯发动的唯二两起恐怖袭击事件。[7]我们不会为此类针对平民并危及“两国方案”的恐怖主义行径辩护,但我的疑问在于,依照该文的叙述:“从以色列开始撤出之日起,每撤出一个城镇,当天或者第二天上午,哈马斯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制造一起公共汽车爆炸事件。”我并不清楚该两次袭击前夕以色列撤出了哪座城镇。我想教授所指应该不是一年多前以色列依照《奥斯陆第一协议》补充协议率先象征性撤离的加沙与杰里科。(象征性在于以色列军队仍可以自由使用当地道路等等[8])且我并没有注意到此次规模非常有限的象征性撤离当即引发了任何来自哈马斯的袭击。事实上,文章中的“撤出之日”本身即令我疑惑,因为只有到同年(1995年)9月28日,巴以双方才最终签署了涉及以色列军队分阶段撤出占领领土并向巴勒斯坦政府移交权力的《奥斯陆第二协议》(Oslo II Accord)。[9]
然而就在真正的撤军协议签署后,我们反而注意到,10月5日 大约三万名右翼以色列示威者聚集在耶路撒冷锡安广场抗议政府与巴勒斯坦方面签订的协议,而以色列议会此时正在对该文件进行辩论。示威者们在电视摄像机前一边展示着将拉宾打扮成党卫军军官的海报,一边高呼“拉宾去死”、“拉宾叛徒”、“用血与火将拉宾驱逐”等等。[10]该文强调的“反对土地换炸弹”的口号在这样的集会中或许会显得过于温和。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以色列规模庞大而不断失控的右翼分子们不断向自己的总理进行着攻击与死亡威胁。[11]而与此同时,依照以色列国防军10月18日情报,哈马斯却反而正在与巴解组织进行着有关停止恐怖袭击的对话。[12]两个月后,哈马斯一度公开宣布自己有意停止袭击以色列。[13]我们自然可以怀疑哈马斯的真实意图,但一个明显的趋势在于,《奥斯陆第二协议》签署后,巴勒斯坦方面正在试图控制自身内部的极端势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反而在以色列方面,右翼势力已然失控,犹太教极端分子开始依照教法将拉宾定义为“追击者”(rodef),或一个正在追击另一个人以图将其杀死的人,“处决”拉宾——或右翼集会上类似“拉宾去死”的口号由此得到了“法理依据”。[14]

1995年4月11日,总理拉宾·伊扎克向支持者发表演说。
而就在以色列右翼正在严重危及和谈的紧要关头,10月23日,大洋彼岸的“助力”即时到来——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宣示:耶路撒冷不可分割且应被承认为以色列国的首都,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应不迟于1999年5月31日在耶路撒冷设立。[15]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奥斯陆第二协议》签署后和平真正迫近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美国、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三方内部各自不愿见到“两国方案”最终实现的极端势力中,哈马斯反而是表现得较为克制的一方。而以色列右翼最终亲手葬送了和平的希望——11月4日,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一场支持和平进程的集会结束时遭到暗杀。凶手伊格尔·阿米尔是一位长期参与右翼活动的极端正统犹太教徒,他表示自己依照宗教信条杀死了拉宾以图阻止政府将西岸地区交还巴勒斯坦人。[16]
现在让我们重新阅读殷罡教授的论述:“当这种‘土地换炸弹’重复了很多次之后,以色列的示威口号开始变了,‘反对土地换炸弹’。于是在1995年11月,一个以色列的激进大学生、极端分子,叫阿米尔,在集会上把拉宾打死了。” 在更加全面地了解事情的经过后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逻辑链条是很难成立的。第一,以色列真正的撤离协议,或《奥斯陆第二协议》(9月)签署于同年哈马斯两次恐怖袭击(7月、8月)之后,“土地换炸弹”在拉宾遇刺前“重复了很多次”并不存在事实基础;第二,以色列右翼对于拉宾的仇恨根本出于后者对于和平路线的坚持与撤出西岸地区的决定本身,哈马斯的恐怖袭击可以成为以色列右翼反对拉宾的佐证,但并非决定性或转折性因素。第三,凶手阿米尔刺杀拉宾的动机,据其自身承认,在于极端的宗教信条,而非所谓“反对土地换炸弹”的政治逻辑。据此,我认为教授的论述在缺乏现实依据的情况下,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内部各自的极端主义,或反和平势力间建立了一种“先后顺序”或“因果关系”。这样的论述无法成立,也因而很难支持殷罡教授的最终观点,即在此期间破坏奥斯陆协议与巴以和平的主要责任或首要责任(而非一般责任或重要责任)在于哈马斯。我或许会因直觉接受教授的推论,但我们需要真正的论据。
且我同样认为,在以色列右翼势力煽动下与宗教极端主义信条驱使下刺杀拉宾的凶手阿米尔于情于理均不值得一个“哈马斯炸弹袭击在前”的上下文。我如殷罡教授一样相信恐怖主义是一种绝对之恶。
3.关于利库德
教授同时在文章中描述了拉宾死后他在公交车上看到的一幕:“一帮小青年,都是利库德(以色列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在那说‘拉宾死了!’‘拉宾死了!’。一个女孩子,工党的,就斥责他们。之后小青年就不说话了。”我再次感谢文章提供的宝贵的历史细节,但文章未能告诉我们的是,利库德(Likud)并不只是一个所谓的“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它是以色列国1977年至1992年之间绝大多数时间里的执政党。而利库德的前身、梅纳赫姆·贝京(第六任以色列总理,利库德集团创始人)领导的伊尔贡及其衍生的政党则在爱因斯坦与汉娜·阿伦特等知名犹太学者口中有着十分负面的评价。[17]利库德的党纲中明确表示:“‘朱迪亚-撒玛利亚’(西岸地区)不会被交给任何外国政府。在海与约旦之间,只有以色列主权。[18](1977年版);约旦河将是以色列国永久的东部边界(1999年版)。[19]”——就像哈马斯否认以色列国一样长期性、系统性地否认巴勒斯坦。

在2009年,以色列国会选举中利库德集团的宣传横额。
且时至今日,内塔尼亚胡领导下仍在以色列长期执政的利库德仍会在自己的官网上骄傲地宣示:“在贝京的领导下,利库德在朱迪亚-撒玛利亚与加利利举起了犹太人定居点的旗帜,制定了《耶路撒冷法》,确立了统一的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国首都的地位。”[20]在补全这样的信息后,我们很难得出破坏“两国方案”的首要责任(而非重要责任)在于哈马斯的结论。我真心希望历史的进程可以如该文所描述得细节那样美好:“(利库德成员)在那说‘拉宾死了!’‘拉宾死了!’。一个女孩子,工党的,就斥责他们。之后小青年就不说话了。”而事实上,利库德集团非但没有“不说话”,反而说了许多话——许多破坏两国方案与和平进程的言语,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仍在主导以色列政坛。
4.关于“愤怒的葡萄”行动
同样地,请先阅读了解该文的叙述:
“葬礼过后,以色列的民情又发生了转折,从一开始的支持‘土地换和平’,到迟疑‘土地换和平’,到坚决支持‘土地换和平’,继承拉宾的遗志。这个时候一股新的力量加入搅局,就是黎巴嫩真主党。
当时以色列要进行新的大选,哈马斯那时候比较消停,因为加强防范了,真主党出来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佩雷斯当时作为自动替补的看守政府的总理,就发动了一场“愤怒的葡萄”行动反击。真主党把火箭发射器放在联合国营地后面,而恰恰一百多个黎巴嫩难民(阿拉伯人)躲在联合国营地里避难。以色列的炮兵自动反击系统就引导一门重炮打这个火箭发射基地,正好落在屋顶上,这一百零几人死伤殆尽。这一下以色列阿拉伯选民不干了,打真主党别杀阿拉伯人啊。1996年5月,以色列举行大选 …… 结果由于阿拉伯选票占以色列全部选票的20%,放弃参选,很多犹太人也觉得工党把事情搞砸了,换个人试试未尝不可。于是内塔尼亚胡以不足1%的优势胜了佩雷斯。
这一下,哈马斯和真主党联合的颠覆势力,可以说就把和平进程给阻断了。”
首先我想指出一个事实问题:“以色列的炮兵自动反击系统就引导一门重炮打这个火箭发射基地,正好落在屋顶上,这一百零几人死伤殆尽。”这句话似乎并无事实依据,因为即便在偏向以色列的叙述中人们也不会否认,这枚袭击卡纳(Qana)联合国营地的炮弹是一支侵入当地的以色列特种部队主动呼叫火力支援的结果并人为发射于一门M109自走炮。[21]我很难接受教授有关“炮兵自动反击系统引导一门重炮”的说法。因为并不存在的“自动反击系统”不具备甄别联合国营地与难民情况的能力与责任,而这恰恰是联合国大会决议要求以色列至少以经济补偿的形式承担的责任。[22]
且有关该事件的争议远远不止于此,据由联合国荷兰籍军事顾问弗兰克林·范卡潘少将(Franklin van Kappen)提供的联合国调查报告显示:“在炮击期间,(以色列)火力可感知地从迫击炮阵地转向了联合国营地”;且“与(以色列方面)一再否认相反的是,炮击发生时卡纳地区出现了两架以色列直升机与一架遥控飞行器”。连同其他若干证据,报告认为:“严重的技术和/或程序失误不太可能是导致联合国营地遭到炮击的原因”。[23]遗憾的是,该文未能指出该事件中存在的严重争议或提醒我们联合国调查报告的存在。
介绍过这一细节后,让我们整体讨论“愤怒的葡萄”行动。该文显示,“(1996年)这个时候一股新的力量加入搅局,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当时以色列要进行新的大选,哈马斯那时候比较消停,因为加强防范了,真主党出来向以色列发动袭击。”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真主党并不是一个“新的力量”。因篇幅有限我无法从头介绍黎巴嫩内战与真主党的起源,但需要注意的是,在1985至2000年期间,以色列始终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划有着一片所谓的“安全区”并依靠基督教民兵组织“南黎巴嫩军”(SLA)维持着自己在黎巴嫩领土内的军事存在。在此期间,真主党与南黎巴嫩军及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始终没有结束。1993年7月,真主党与以色列仅仅达成了口头上的停火协议。但双方事实层面的冲突与交火从未停止。[24]例如1994年6月,以色列空袭杀死了30至45名真主党成员[25];1995年3月,真主党一位高级领导人遭以色列暗杀。[26]两个月后,又有4名真主党成员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交火身亡。[27]翌年2、3月份,依照联合国报告显示,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占领军(包括其扶持的民兵武装)与当地包括真主党在内的各派武装之间冲突继续加剧,以色列军队出现伤亡。3月30日,黎巴嫩南部小城亚塔尔(Yatar)遭到以色列导弹袭击,两名正在水塔工作的平民遇难,另有一人受伤。真主党随后向以色列本土发射火箭弹还击;一周后,黎巴嫩南部一处炸弹装置爆炸导致一名男孩遇难另有三人受伤,真主党表示有证据证明炸弹来自以色列军队,尽管后者否认,真主党再次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真主党两轮火箭弹造成数人受伤,无人死亡。以色列随后向火箭弹发射区域投下9枚炸弹并发射约250枚火炮进行还击。[28]以色列方面“愤怒的葡萄”行动随即于4月11日开始。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不难发现,自1993年以色列与真主党签订口头协议以来,双方之间的冲突从未真正停止且绝大多数伤亡均发生在黎巴嫩境内。3月30日冲突再次危及平民后,双方的行动均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对等还击”。在这种不断持续的冲突中讨论诸如“谁先动手”的问题似乎是一种徒劳,且若果真需要探究冲突的根源,那么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南部的持续占领与破坏,连同其扶持民兵武装的行为(即对于联合国安理会1978年通过的425号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刻自所有黎巴嫩领土撤出其部队”[29]之违背)或许才是当地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这样的占领正是黎巴嫩真主党诞生、壮大并令冲突逐渐宗教化的必要因素。
因而我难以同意教授有关拉宾死后,真主党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加入搅局”的说法,更难以认同其有关“真主党出来向以色列发动袭击”试图影响以色列大选,并最终导致右翼内塔尼亚胡在选举中战胜佩雷斯,以至于“把和平进程给阻断了”的论述。这似乎是一个典型的“事后归因谬误”:“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发生在“佩雷斯败选”之前,于是便成为了后者的原因——但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如果真主党果真计划通过袭击影响1996年的以色列选举(我非常希望听到有关于此的具体证据以扩充自己的知识),并相信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那么他们想要怎样的结果呢?如果希望佩雷斯败选,那么他们又怎能预测到卡纳联合国营地遇袭的小概率事件呢?而若行动依照大概率进展,即佩雷斯“在剿灭大批恐怖分子后得胜归来”,那么佩雷斯又怎会败选呢?

当地时间2023年11月3日,贝鲁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自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讲话。
而在了解这一简单的逻辑错误后,我们还将看到更加有趣的事情——在此轮冲突中主动试图急剧升级局势的一方反而是发动“愤怒的葡萄”行动的以色列。我将引用以色列官员们自己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官网介绍“愤怒的葡萄”行动的文章直接引用了时任以色列空军司令赫茨尔·伯丁格(Herzl Bodinger)本人的说法:“此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国家和外交层面创造最佳条件,以便与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谈判。”国防军官网据此继续介绍:“这一想法的实施涉及对基础设施的攻击,以带来附带的经济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损失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影响居民和黎巴嫩政府。”[30]
行动第五天,当时正担任以色列外交部长的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电视采访中同样直白地表示:“我认为叙利亚人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多年来在黎巴嫩的投资,包括建立现任政府、带来相对繁荣并开始重建贝鲁特,如今都已因我们破坏贝鲁特电力基础设施等行动而面临风险。我认为所有这些观点都说明了我们具有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叙利亚无法置身事外的事实。”[31]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以色列发动“愤怒的葡萄”行动侵入黎巴嫩的重要考量在于叙利亚。接下来我将解释为什么是叙利亚,以及为什么时间节点会在1996年以色列选举之前。
我将引用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1993年至1996年间以色列对叙利亚首席谈判代表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教授(Itamar Rabinovich)本人的说法。佩雷斯的确在拉宾遇刺后继承了他的政治政策与路线,但这些政策不仅包括巴以问题,同时还有与叙利亚和解的问题。克林顿非常希望尽快促成以色列与叙利亚和解,拉宾遇刺后,他第一时间询问佩雷斯是否愿意继续谈判,后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1995年继任总理后,“佩雷斯表示愿意优先考虑叙利亚问题并迅速达成一项协议。 但(老)阿萨德并没有以同样的热情做出回应。佩雷斯的风格似乎是在恐吓阿萨德,且佩雷斯越焦急,阿萨德便越不愿意谈判。阿萨德不够积极的原因有很多。阿萨德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佩雷斯在安全问题上比拉宾更加灵活……且佩雷斯有关经济合资的提议远远超出了阿萨德的兴趣范围……此外,美国方面有关在以色列选举前达成协议的诉求并没有动摇阿萨德——他并不觉得工党与利库德集团之间存在区别因而并不着急。”[32]

2014年2月25日, 以色列耶路撒冷,佩雷斯在集会上发表演讲。
于是,急于谈判的佩雷斯会产生怎样的考量呢?是的,“在国家和外交层面创造最佳条件,以便与黎巴嫩和叙利亚进行谈判”;亦即证明“我们具有对叙利亚采取行动的能力,以及叙利亚无法置身事外的事实”——这正是前文中佩雷斯的空军司令与外交部长对“愤怒的葡萄”行动做出的解释。至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以解释以色列为什么会在1996年选举前的时间节点,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已久的冲突中以超出“对等回应”的方式发动“愤怒的葡萄”行动并使局势急剧升级。佩雷斯此次行动的目的绝非单纯在于还击真主党,其真正目的在于尽快促成与叙利亚的谈判并在谈判中获得更好的筹码。这并不会影响我们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真主党如以色列军队一样在冲突中危及平民的行为本身。但在了解上述历史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该文的叙述呢?
这个时候一股新的力量加入搅局,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当时以色列要进行新的大选,哈马斯那时候比较消停,因为加强防范了,真主党出来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佩雷斯当时作为自动替补的看守政府的总理,就发动了一场“愤怒的葡萄”行动反击。(随着卡纳惨案的发生与行动的失败)内塔尼亚胡以不足1%的优势胜了佩雷斯。这一下,哈马斯和真主党联合的颠覆势力,可以说就把和平进程给阻断了。
这似乎是一种从结论出发倒推历史的叙述,且叙述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信息偏失与逻辑失误。
最后,让我们暂且忽略以上一切不容忽视的讨论而单单聚焦于以色列国防军官网上有关“愤怒的葡萄”行动的另一条叙述:“行动期间,黎巴嫩南部的什叶派村庄遭到轰炸,其目的在于促使平民向北迁移至贝鲁特,从而迫使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对真主党的行动进行具体打击。”[33]且不论黎巴嫩政府对这样的目标提出了严词谴责[34],且行动本身即因联合国营地遇袭并出现大规模平民伤亡而最终失败——当我从“法理”角度看待该问题时,我所找到的唯一一条与此相关的法理即是《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一议定书)》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平民居民本身以及平民个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禁止以在平民居民中散布恐怖为主要目的的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35]
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法理”而单单出于“情理”地将讨论停留在对于一切恐怖主义行径的谴责,因为轮回般的恐怖袭击与报复行为从不会因谴责而消失。且我们无法忽视历史留给我们的任何信息与细节,更无法急于从任何细节中得出确凿的结论。历史的全貌是学者们求而不得却永远不应放弃追求的事物。否则历史的重演将成为人类的宿命——“(以色列军队)行动期间,……村庄遭到轰炸,其目的在于促使平民向北(南)迁移……”这是27年前的黎巴嫩,亦是此时此刻的加沙。
5.关于戴维营谈判与加沙问题
在讨论2000年的戴维营谈判时,该文忽略了这场谈判的后续,即2001年初的塔巴谈判。在谈及土地问题与耶路撒冷地位问题之余,文章忽略了同样重要的“难民问题”与“安全问题”。有关巴勒斯坦方面在四大问题上的具体关切,读者可参考巴方谈判团队给出的有关自身立场的详细报告。[36]关于文中所提到的:“巴拉克提出的方案是交还巴勒斯坦土地的93%,有的人说95%(这是我亲耳听阿巴斯讲的,他是参加过谈判的),再通过少量的土地置换求得一个平衡”。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以色列交还90%以上土地的巨大“让步”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以色列希望得到的领土”的让步。巴勒斯坦方面有理由依照现实情况将其理解为“以色列将永久吞并一定比例的巴勒斯坦土地”——这显然仍是一个需要谈判的问题,且巴方谈判团队在刚刚引用的报告中详细指出了这样的问题。
巴方认为,此类百分比说法所涉及的土地总面积并未得到定义,这意味着特殊定义下的“耶路撒冷”、“无人区”与“死海”概念有可能令以色列实际吞并的面积达到10%。同样重要的是,若我们将2001年年初作为戴维营后续的塔巴谈判纳入考量,那么巴勒斯坦方面恰恰因为阿拉法特在戴维营的强硬态度而得到了更好的条款。对此,即便是亲自参与谈判的前以色列外交部长施罗默·本-阿米(Shlomo Ben-Ami)亦曾明确表示:“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我会拒绝戴维营”。[37]至于这场注定艰难而反复的谈判究竟为何未能继续,其答案显而易见——以色列很快于2001年3月迎来了强硬的右翼总理阿里埃勒·沙龙。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历史事实,因为“让时间停在戴维营”的历史叙述与将和谈破裂的责任完全投向阿拉法特与巴勒斯坦一方的做法只会令我们错失有关沙龙上台与以色列政坛持续右转的讨论——这将阻碍我们全面探究“两国方案”难以实现的真正原因。
此外,该文表示2005年以色列对于加沙的占领状态“已经结束”且符合“国际法标准”。这样的判断本身极具争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于,以色列在“撤离”后依然对加沙实施着领空、海岸与边界的控制且将单方面决定加沙是否可以开放海港或机场。依照“撤离计划”,以色列仍将控制加沙所有过境点,包括加沙与埃及的边界,且以色列将继续在加沙地带海岸线开展军事活动。[38]这些内容显然超出了以色列国管控自身边境的范畴。我们至少需要告知读者相关争议的存在并鼓励人们在形成任何观点前主动寻求更加全面的信息。
6.关于1948年以前的历史问题
最后,我将简要探讨该文开头有关1948年以前巴勒斯坦历史的相关问题。文中表示:
在1923年到1947年,巴勒斯坦是受到英国直接委任统治,它认为这里不适合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因为耶路撒冷是三大一神教的圣地和发源地,这里的民族教派复杂,宗教政治问题敏感。所以英国就对它实施委任统治,别的地方可以逐渐逐渐独立。

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
这样的论述似乎忽略了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的真正原因——即殖民利益的考量。英国在一战过程中占领巴勒斯坦的重要目的之一即在于确保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侧翼的安全。此外,海法是英国殖民规划中极为重要的地中海港口——依照1931年的工程计划,一条东起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地区、西抵地中海海法港的输油管道每年将为英国人提供至少三百万吨石油。这些石油将保证英国舰队的燃料需求在英国人自己控制的领土上实现自给自足,其对于英国海上霸权的重要意义因此不言而喻。[39]这条管道如今早已废弃,但我们仍可以在地图上轻易找到它的大体位置与走向:今天约旦王国版图东北部一块深入沙漠的“鼻子”与伊拉克版图西部的凸起,以及两片土地,或两国之间仅有180公里宽的边界事实上即是这条管道的连接处——处于英国控制下的外约旦与伊拉克由此将这条重要的输油管道安全地包裹在了自己的领土之内。至于作为管道终点的海法港与巴勒斯坦海岸,这里更是英国人不容有失的殖民地。
此外,该文表示:
二战之前,英国一开始想把这个地区组建成一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共享的国家,有英式的议会,有不同族群的代表等等。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有激烈的冲突。犹太人的志向不是以现有的几万人占个少数的议席参与这个地区的政治,他们想在这边建一个大家园收容各地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当然不愿意。
这样的叙述再次忽略了英国托管政府的殖民性质。英国方面的计划从来不是秘密:在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亚瑟·万霍普(Arthur Wauchope)看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将持续生活在自己的托管统治之下,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人口比例或可达到40%)将凭借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与阿拉伯人形成平衡,而一种“良性”的种族分裂将为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提供便利。[40]因而所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有激烈的冲突”并不是英国人对于这片土地的客观观察,而是他们的殖民需要。
至于下一句论述:“犹太人的志向不是以现有的几万人占个少数的议席参与这个地区的政治,他们想在这边建一个大家园收容各地的犹太人,阿拉伯人当然不愿意。”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目标绝不只是“建一个大家园收容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的目标在于无视巴勒斯坦已有人口结构而通过移民活动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收容各地犹太人”的被动诉求反而是锡安主义者们改变巴勒斯坦人口结构的积极需要。且他们并未试图与当地阿拉伯人沟通所谓“收容各地犹太人”的“合理诉求”并得到“阿拉伯人当然不愿意”的答案。有关于此,即便是以温和著称的锡安主义领袖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未来的第二任以色列总理)亦曾明确表示:“犹太人从少数变为多数的过渡阶段对于锡安运动至关重要。该阶段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英国人与美国人,而非阿拉伯人。阿拉伯人并没有最终的话语权,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整个世界上。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与阿拉伯人接触并与他们达成共识,让我们放弃这样的观点。”[41]
文章随后提到:
“英国人在二战前也曾试图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分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就是1937年出台的‘皮尔考察团分治方案’,但双方都嫌分给自己的面积小,英国的共享方案和分治方案都破产了。”
我们如今不难找到皮尔考察团报告的原文。[42]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的发布背景是1936年至1939年之间巴勒斯坦地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而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巴勒斯坦当地的人口结构刚刚在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1931年至1935年之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总数由原本的17万人左右直线上涨到了近40万人,其占巴勒斯坦地区人口的比例则由17%增长到了约30%。[43]
也即是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此时正在激烈反抗持续已久的英国殖民统治与该统治下源源不断涌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而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尔报告在假设英国殖民秩序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为这片土地做出了最为符合英国利益的安排——依照报告,犹太人将获得内盖夫沙漠以北直到黎巴嫩边境的整片海岸地带以及北方的整个加利利地区,英国人将继续控制耶路撒冷与伯利恒周边地区及一条通向雅法港的走廊,而阿拉伯人则将获得其余以内陆为主的地区。委员会同时提议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依照分治方案进行人口交换,而所谓“交换”的首要现实意义即是将阿拉伯人大规模迁离巴勒斯坦海岸。至于过去数年间刚刚来到巴勒斯坦并刚刚显著改变当地人口结构的犹太移民,他们非但没有任何可供“妥协”的事物,反而快速得到了一座用以将巴勒斯坦人口结构“新现状”化为永久现实的国家。且更重要的是,皮尔委员会的所谓“分治”方案与今天的“两国方案”具有本质区别:英国人希望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并入外约旦——一座当时同样处于英国托管统治下的国家。
简言之,皮尔委员会的报告在承认托管统治难以为继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维护了英国自身的利益。除了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将继续接受殖民统治外,英国人为分裂的巴勒斯坦挑选了自己最为信任的统治者。在潜在的条约体系下,无论是锡安主义者还是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理论上都不会介意接受一份对伦敦当局极为有利的条约以维系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基于这样的认识,让我们重新回看该文的论述:“英国人在二战前也曾试图将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分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这就是1937年出台的‘皮尔考察团分治方案’。”这样的说法似乎忽视了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并在当时与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治”方案间建立了联系。
且该文随后的论述,即“双方都嫌分给自己的面积小,英国的共享方案和分治方案都破产了”同样存在问题。犹太群体内部的主流意见并不排斥皮尔委员会方案。在包括本-古里安与哈伊姆·魏茨曼在内的众多锡安运动领袖看来,分治方案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事实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座犹太人的主权国家本身即是锡安运动的意义所在,在这座主权国家之内,犹太移民的规模将不再受到任何外来限制。魏茨曼对此直白地表示:“即便这座国家只有一块桌布大小,犹太人也不应该傻到拒绝它。”[44]至于阿拉伯人,他们反对皮尔委员会方案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其“分给自己的面积小”,而是在于“分治”本身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在该分治方案中的延续。
文章末尾,我希望感谢殷罡教授的论述与文章为我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诸多重要历史问题的契机。本文的唯一目的即在于补全该论述中所缺失的重要历史信息并对一系列似乎与史实相左的问题进行讨论。我希望人们对于巴以问题的了解可以在这样的讨论中得到补充,并且我希望这样的补充依然只是人们深入探究相关问题的开始。
注释:
[1]
[2] 下有关1995年的信息来源于联合国难民署网站Minorities at Risk Project, Chronology for Palestinians in Israel, 2004, available at: ],我同时将对具体引用内容进行核查。
[3] /
[4]
[5] /
[6]
[7]
[8]
[9]
[10]
[11] 同上。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24] Finaud, M. (2015). The 1996 “Grapes of Wrath” Ceasefire Agreement and the Israel-Lebanon Monitoring Group: A Model of Successful Negotiations in Conflict Management. In Negotiating in Times of Conflict.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173-192.
[25]
[26]
[27]
[28]
[29]
[30] /
[31] Israel TV Channel 1, Jerusalem, April 15, 1996,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April 16, 1996, p. 37. 转引自
[32]
[33] /
[34] 例如” 标题下第六段。
[35]
[36]
[37]
[38] /
[39] Bonné, A. (1932). The Concessions for the Mosul-Haifa Pipe Line.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64 (1), 116-126. 120.; 126.
[40] Shapira, A. (2012). Israel: A history.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85.
[41] Flapan, S. (1979). Zionism and the Palestinians. London: Croom Helm. 283.
[42] /
[43] 数据综合引用自Shapira, A. (2012). 81.; Hyamson, A. M. (1942). Palestine: A Policy. Methuen & Co. 147.; Swedenburg, T. (1988). The role of the Palestinian peasantry in the Great Revolt (1936-1939).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Reader, 467-502. 482.; Adorno, M. L. (2008). De Clementi’s Report: The Nineteenth Zionist Congress, Lucerne, 1935, as Viewed by an Italian Diplomat. Israel Affairs, 14 (2), 288-300. 296.
[44] 转引自Shlaim, A. (1988). Collusion across the Jordan: King Abdullah,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the partition of Palest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58.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XX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XXXX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